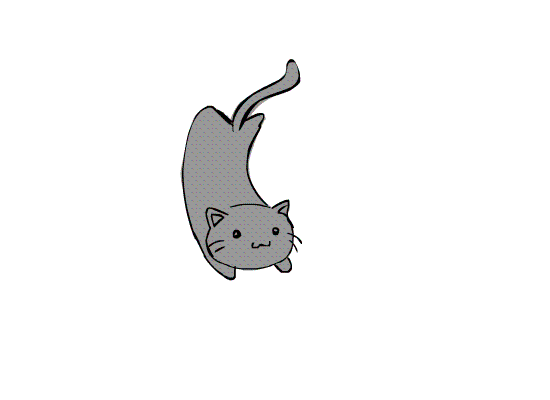周日夜晚
惨月一镰禁天心,霜云散尽见月临 他咀嚼起了那二十三号刀片,就着齁甜的乙二醇,和几十粒喹硫平。 他的嘴唇间已满是伤口与鲜血。 他啐了一口,血色的沼泽, 在身体上刻下贝多芬的月光。 然后如抚摸宝贵的勋章一般一次又一次轻柔地抚摸它们,刀尖创造的血的生命。 或是用指甲开启伤口,又温柔地吮吸或多或少,或匍匐或蹒跚或流涌的鲜血,一次又一次, 流出的生命。 血尝起来是有甜味的。 他盼望着自己早些感染,早些迎来ICU中的自然死亡。 于是无辜的绿色飞虫被他塞入红黑黄相间的伤口。 剧痛。 于是他又塞了些尘灰与沙粒与离自己很近的马桶里的水进去。 疼痛。 他坚信自己的行为没有任何不正常。 但仍因为爱人镜像的行动——割伤自己,感到悲伤。 乙二醇的甜味逐渐在口腔中发酵,口腔逐渐变成了金黄色的巨大蜂蜜山洞,齁甜齁甜的。 他有选择自己作为什么的权利。但也因这权利自责而欲自尽。 他坚信自己对自己所做的一切的真正的正确, 且在尽可能减小与他人的摩擦或任何关联。 他的自我肯定来自于自我否定的尘墟,否定的终结。 为了生存,他必须肯定自己,他又倏忽发现这肯定带给人如此的轻松, 成为自己的寻死的信念的上帝。 自杀是极美之事...
我度过了幸福的一生
我度过了幸福的一生 精神病院是否类似为了预防犯罪而提前将病人逮捕呢?即使是所谓自愿,但人怎会有放弃自由的自由。 人们怎能因为从未做过的事而付出代价呢? 对于有危害性的精神病人,或许只能在他们发病之后审判了吧?令人头疼的问题。 在父亲的葬礼上我一点也不因为他的死而感到些许沮丧与悲伤,唯一印象深刻的只剩葬礼那令人生理不适的气氛,管弦呕哑,哭啼遍野。 从小学一年级到初中一年级的七年间,我只有寒暑假会与他们相见。其他时刻完全可以用渺无音训来形容。或许在某个时刻,他被我远远地抛到幼儿园地童年了,整个小学里,接近我的只有爷爷奶奶。 即使是在寒暑假,我也开始怀疑我对父母的笑是否是一种天衣无缝的伪装了, 真笑与假笑的区别或许就在于,是否可以随心而立刻停下。现在我对母亲的许多笑,显然是主动的,受控制的笑。 老莱娱亲似的。 存在回忆中的有几件事:低年级的我因为生气而回绝了跟母亲的许多次电话沟通,但随后收到母亲送来的塑料小兵人玩具时,愧疚与喜悦的并存似乎说明了我的生气同样是伪装的。伪装的情绪。 因为听班主任说,某同学家长在外工作,便驱车数百公里而来学校开短短的一次家长会…班主任莫名其妙的赞扬令当时的我...
青春的色彩
青春的色彩 如雨后初霁,远远天空上那缤纷的丝带,新生的阳光焕发着色彩。在人生起点的青春,谁将我们染上不同的颜色?我们自己。 青春是赤色的,如才撕开黑色混沌的天空中出现的朝阳,肆意的激情,向广袤的世界挥洒出无限的金光。我们还有着鲜明的梦想,还有着诗和远方,还有着改变一切的狂妄。 俱怀逸兴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 将自己深埋于书山,遨游于题海。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纵有巨浪滔天,承载梦想与希望的小舟不灭;漫天灰云墨雨,不能迷惘灼热的赤色双眼,相信奇迹一定会从远方,再次出现。 赤色温暖的心中的火焰,让我们得以无畏于凌晨五点的寒冰飞雪,从床被一跃而起,就如此开始一天的学习。 教室中的书声先于懒惰的太阳将世界唤醒,一片黑暗之中,我们仿佛带着光。操场上奔跑的我们不畏惧沾满脸颊的汗水与泥土,一串串飞洒的汗珠是活力的象征。 青春也是温暖的橘黄色。 漫漫夜路里那守望在路旁的,一盏黄黄旧旧的灯,仿佛专门等待着你的到来而独自在夜中待了如此之久。这就是那温暖的友谊。当单薄的身体在寒风中颤抖,当无力的双手在冰雪中麻痹,当空洞的视线在白色风暴中模糊,友情便是远远的那等待着你,在飞雪中稳稳...
小故事三则
第一则 她独自站在天台的边缘。 摘掉了眼镜, 灯火朦胧了远处的视线。 灯火藏匿于身前,方形的玻璃与蓝色砖土之后。 一只蝙蝠忽然飞掠,惊动窸窣的鼠群。 夜风吹起她的裙边,吹落她的身体,阖上她的双眼, 吹走了这个世界。 第二则 她是整座学园里最优秀的孩子,她简直就是光。 任何场合下她总是最引人注目。 她的座位在临窗的角落,阳光无时不洒向她的书桌, 窗外无时不有夏季的白色飞鸟,低吟着各色的歌,次次飞过。 她当时微微笑着向老师与同学们的目光眯起右眼,左手在空中画了一个圈, 便笑着跳下了四楼, 那声巨响也没能将那些呆滞的目光唤醒。 第三则 夜已深了。 她看看桌子左侧,唯一的灯火正在闪烁。 书桌上摆着十二粒喹硫平,两瓶两百粒扑尔敏,二十粒舍曲林,十粒劳拉西泮, 一百毫升的苯,一百毫升的乙二醇。 她想去一个没有人的地方, 且永远永远永远不会有人的地方。 她如此害怕人们,她想要去没有人类的地方。 她逼视着破碎镜子中狰狞的面孔,指责她的人说:“你去死。” 写于 2020.10.13 晚自习
对我自己的分析
隐隐得出的结论是,我的思想太复杂。 曾将自己的一切行为视为对他人的否定,以至于存在本身也被视为一种罪过。叶藏便是在这种心态下,祈祷并离开纯子。不过在学校里我哪有离开的权利,因为我将离开学校也视为一种罪过——对他人的否定了。——一段内心独白: “你们都很善良啊,待我真的这么好。但我为什么还会是这个样子?只能是我自己的责任了,没有一个人辱骂我,欺凌我,嘲讽我——诸如上述的一切无论客观还是我主观看来,都是你们从未做过的。但我处于痛苦之中的事实,我确信无疑。那么剩下唯一可能的选项便是我自己。一切的原因是我在精神自残。我只能白费你们的关心,而竟从未做出任何好的回应?虽事态在好转——我对你们坏的影响在一步步缩小。至少在行动上,我越来越透明。但我仍在恐怖着污染了你们的视线。于是不作为也包含着“存在着”这作为。我又在以“存在”这作为,来否定你们了。 世界是肯定的舞台。而我远远地躲在一角不敢呼吸,惊恐行为中任何否定的成分于是放弃行为。我的痛苦源自于对否定的不满足——存在,与自我肯定。否定否定的失败,否定在否定着除它自己之外的一切。 唯一对我影响较大的,PTSD的,也就2018年夏天,脑海中浮现出的...
如何用叔本华的理论来解释叶藏
从来只是否定着自己的人畏惧他人的对自己的意志的肯定。 因为隐隐透过个体化原理,他意识到这次对自己的肯定如此强烈。纵使这肯定不由他自己做出,这肯定亦增加了意志肯定的绝对值,透过根据个体化原理,这也是对于对方的否定,同时也是自己对于对方的否定。 这是自己对于对方的,从前从来不敢做出的,现在却被对方自动做出了的,对他人的否定。 叶藏的敏感将此视为杀人一般的罪行。 于是叶藏在门后跪地祈祷着,被自己所杀的爱人可以从自己幻想的痛苦中解脱。为了避免自己做出更大的罪行————否定,而逃离。 叶藏隐隐看破个体化原理,于是被称作“神一样的孩子”。 即使他们所有人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推断写于 2020.9
金色海洋
夕阳慷慨地将金光撒向全世界的一切活着的意识。他孤单地站在崖边,海风将他的衣摆吹起,蔚蓝的绸缎如波浪般流连。他将左手缓缓抬至身前,松开五指,一滴眼泪——眼泪般的水晶——无数细小的棱角与光面簇拥在一起,闪烁着飘浮在海平面远处的霞光,将那炽热而冰冷的火焰融化成冰冷而炽热的泪滴。他微蹙双眉,神色迷离地望着她的泪水。不知不觉,他的泪水模糊了整个世界。 在她16岁那年,隆重的成年礼使村里的人们为所有16岁的孩子建造了一座桥,一座巨大的桥,一座连接海崖与晚霞的大桥。没有人能记起当桥最终落成时,有多少城邦里的居民前来祝贺,有多少尊贵的国王前来瞻仰,有多少威严的教皇前来祝福。但现在没有人老到能记起村人是如何完成这一壮举的,他们只能记得,当16岁的少女们穿着华美的连衣裙,戴着镶嵌有101粒深海底部蚌壳里的珍珠的手链——这是村人过往数十年的积累——戴着斜插着白羽的丝绸帽子,赤脚走上桥面,越走越远……越走越远……最后却只有她带着装在瓶子里的晚霞归来,而其他的女孩儿们,却都永远地消失在那永恒的晚霞之中。 她很快受到了村人的刻意敌视,她被认为是杀人的刽子手,被认为是值得所有人唾弃的自私者,被认为是灭绝人性的...
梦呓
YS 我有预感我会在最近死去。 这显然不是我第一次如此的预感,现在是2023年12月27日星期三,晚上22:10。 但是没人知道死亡究竟何时会到来。无论怎样的呼号呐喊在最终的结果揭晓前都是出神入化的演技。都不被人重视。我常常忘了吃药。就在昨天我一天补了两天的药量。不得不说,骤然停药很难受,补药也很难受,补了药才能保证数量上完美的精确,才能为这出戏提供完美的细节上的真实。除此之外由于唇裂,我已吃了五天各类维生素,今天6粒B6,6粒B2,6粒C,昨天6,7,7,前天停药,大前天8,13,6,再向前5,11,6,再向前6,15,7。吃药一周好,不吃药得7天。药已然在我生命中占据了相当重要的地位。每天光是吃药就得花上几分钟。柜子散落着六七瓶大小不一的药,拆封与未拆封。桌面上滞留着CM老师送给我的只留下几粒的一盒松子,下面是由于寒冷而暂未表现出腐败的橘子。但是我将如何死去。 他在桥上走过便会把眼神淹没在水里。水泛滥着深绿色。没有轮渡掠过。岸边沉睡着深埋着自己的悲伤的灵魂。栏杆是那么浅,是那么充满信任的高度。然后某人从桥上落下,在某个清蓝色浸润的凌晨,在所有人的视野还没被将消逝的月亮照亮之时...